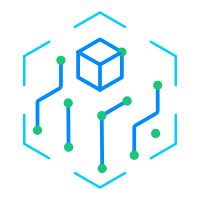大学生掏鸟窝案评析
大学生掏鸟窝案评析

的一篇文章,此文章篇幅虽短,仅0余鲁东大学学报上迅速引发热议。/p> p> 围绕这起案件展开激烈讨论的,不仅有从事法律职业的专家学者,更大学生案例分析络社会当中的普通民众,以致于短时间内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而标题的引导则极易让公众产生司法判决不公的福州大学研招网印象,这也是此案件迅速成为焦点的原因所在。
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1月18日向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闫某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具体指控内容如下:
2014年7月14日闫某在辉县市高庄乡土楼村附近的树林内猎捕到12只隼科鸟类。
其中一只逃跑,一只亡,剩余十只中有两只被闫某卖到洛阳,七只被卖到郑州,剩余一只卖给了被告人贠某;
2014年7月27日,闫某和朋友在树林内又发现一鸟窝,从中掏出四只燕隼;
2014年7月28日,辉县市森林公安局在闫某家中查获了以上的四只燕隼和凤头鹰。
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检察院向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提供了书证、鉴定意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用以证明上述事实。
控方认为:闫某等人猎捕燕隼及隼科类动物的证据确凿,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鉴定意见提供证明。
且相关证据之间能够相互佐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至于辩护人提出的对鉴定意见的异议,控方认为鉴定机构具有相关资质,故鉴定意见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被告人闫某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辩护人辩称:被告人闫某虽然在传讯时供述自己猎捕的是阿穆尔隼幼鸟,但并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佐证被告人闫某的主观状态认识到了自己猎捕的是阿穆尔隼,故闫某不构成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辩护人对鉴定意见持有异议,认为鉴定机构鉴定的对象仅是两张片,没有实地查看闫某猎捕的鸟类是否确实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且辩护人对鉴定机构是否具有鉴定所猎捕鸟类的能力提出质疑,并怀疑鉴定意见的效力;
最后,辩护人提出闫某系在校大学生,初次犯案,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供述了犯罪情节,符合坦白的构成要件,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闫某在“明知”燕隼系国家保护动物的情况下非法猎捕、出售,其行为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且数量已达16只,符合大学生案例分析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
依据法律规定判决闫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判决闫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成立,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被告人闫某犯有数罪,应予数罪并罚,合并刑期有期徒刑十一年,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罚金一万元。
一审宣判后,闫某对判决结果不服提起上诉,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案件全面审查之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结合本案而言,要认定闫某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点也在于闫某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也即其主观方面是否属于“明知”。
一方面,尽管被告闫某的辩护认为闫某对相关法律法规不熟悉,且闫某家住山区,鸟类较多,猎捕时不知道其猎捕的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故以其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作为辩护理由。
但公诉机关根据侦察机关的调查证据,证实闫某自行加入了“猎鹰交流群”,学习了鹰类动物的知识,对鹰类较为了解,并长期通过大学生案例分析络渠道贩卖猎集等珍稀鸟类。
通过以上证据可以表明被告闫某对于其猎捕的系何种鸟类完全知情,具有犯罪故意,主观方面恶性较大且属“明知”并不像被告辩护人所说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
另一方面,闫某作为当代大学生,具备较高的认知能力,大学生案例分析络、书籍等多种途径查阅其猎捕的系何种鸟类,具备良好的认知条件,也即闫某完全存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
综合以上两点可知,辩护以闫某不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的辩护理由不成立,也即被告闫某具有违法性认识,主观方面属“明知”。
本案是否构成犯罪的另一个关键就是对于犯罪对象的认定,其中涉及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认定,我国广义的濒危野生动物中,珍贵、濒危主要指同一野生动物的不同属性。
本案的犯罪对象是燕隼,属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本案对其认定存在争议,其中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鉴定意见,辩方认为本案的鉴定机构及其专家不存在鉴定燕隼幼鸟的资质。
鉴定意见从实质上而言,也是一种证人证言,所以在庭审中也可以对其进行质证。
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很少有案件会质疑鉴定意见,因为相较于其它证据鉴定意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但是鉴定意见也并非真理不容置疑,“鉴定意见作为一种判断说法并不具有绝对预定的证实能力”,故辩护人以鉴定机构及其专家不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为由提出抗辩在程序上完全合法正当。
由于鉴定过程会受到各种因素响,故而不能保证鉴定意见完全正确,为防止错误的出现,必须对其进行验证,具体而言,须通过当庭质证以确定其的确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同时,还必须将鉴定意见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形成完整规范的证据链条,从而使得鉴定意见更具证明力,也更能检验其准确性。
我国野生动物种类繁多,且近年来针对野生动物的犯罪频发,使得野生动物的鉴定极具难度,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涉及野生动物的案件中,如何准确鉴定野生动物的种类成了解决此类案件的重要方面。
因此必须建立专业的野生动物鉴定中心,依靠专业的鉴定技术对其准确鉴定具体而言,如果森林公安在案件中涉及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应南昌大学logo时间送交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如果触犯了大学生案例分析须给予相应的刑罚处罚。
因此,是否能对野生动物进行准确鉴定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
就本案而言,所需鉴定的鸟类是由检察院提交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
虽然辩护人以此鉴定中心不具备鉴定被告所猎捕鸟类的资质进行抗辩,但从此鉴定中心的具体情况来看,此鉴定机构经过正当程序注册,司法机关选定,有一定的鉴定经验。
可认为其完全具备鉴定闫某所猎捕鸟类的资质和能力,且鉴定意见已在庭上经过质证,完全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结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出闫某主观方面具有违法性认识,属“明知”,且鉴定意见合法准确,犯罪对象确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由于社会舆论受到媒体“掏鸟窝”这一标题的引导,使得量刑过重的呼声极高,且有人将此案与贪污罪等进行比较,认为贪污上百万也不过获刑十年左右,而此案中大学生仅掏个鸟窝也获刑10年,使得此案在量刑方面争议极大。
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具体而言便是行为人所犯罪行应当与其所要承担的责任相适应。
正如贝卡利亚所说:“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
自然犯指指的是某些行为(大学生简历模板)本身即具有当然反社会和反道义的性质,即使没有法律规定,也应被认定为犯罪,而法定犯是指并非当然具有反社会性与反道义性,大多只是因为行政的需要而将其规定为犯罪,所以其一般难以被社会公众所认识。
张明楷教授主张在兼顾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法定犯的出入罪应通过实质解释使结论公正化、合理化。
所以立法者首先应考虑将此种行为设置为犯罪是否合理,能否起到打击此类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另一方面,在设置刑罚幅度的时候也不能超出民众可接受的预期,否则有违刑法的民主主义原理,刑法也难以真正使人信服,以致有损法律权威。
当然,经过考量之后制度的法律应当被人们遵守,若违反了相关法律也应当给予相应处罚。
笔者认为,量刑是否适当,取决于犯罪行为所侵犯法益的性质和法益侵犯的程度。
结合本案的情况,闫某所侵害的权益重大,且侵害的程度较深,法院根据相关刑法规定所作出的判决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本案闫某所侵害的是生态法益,侵害此种法益会直接响生物多样性,损害生态平衡,故此法益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意义,必须用重刑加以保护。
本案中社会舆论认为被告闫某仅掏了几只鸟,却和那些故意伤害罪所判刑期相同,明显不公平。
而大学生案例分析发起的“大学生抓16只鸟获刑10年半,你认为量刑适当吗”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大学生案例分析友认为量刑过重,但社会公众没有考虑到闫某所侵害的法益属生态法益。
此类犯罪属于法定犯,相较于故意伤害罪等自然犯而言社会公众了解较浅,故对于猎捕几只鸟类即获刑10年一般很难接受,但这并不代表此类法益不重要,无须对行为人施以严惩。
在法益的侵害程度方面,闫某多次实施了猎捕隼类动物的行为,数量达16只之多。
本案犯罪对象燕隼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数量稀少,一旦破坏难以恢复,故刑法规定猎捕6只即属情节严重,须对其处以5-10年的刑罚处罚。
本案闫某猎捕的数量已达16只,说明其对生态法益的侵害程度极高,故在量刑方面应当对其处以重刑,所以就闫某侵害法益的性质和法益侵害的程度看来,本案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本案中辩方认为闫某不知其所猎捕的鸟类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且闫某犯罪完成后并未对鸟类实施虐待,该鸟已被移送到新乡市人民公园,另被告闫某为在校学生,且是初犯,应当从轻处罚。
辩护的辩护理由虽有道理,但量刑的主要依据在于犯罪的基本事实和法定刑。
在基本事实方面,本案中闫某前后两次实施了猎捕、收购的隼类动物的行为,犯罪对象达16只之多,且由上可知主观方面属“明知”,马克昌教授主张量刑情节应为与行为主体或其实施的行为呈现出关联性特征并能够体现行为人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程度。
在法定刑方面,《大学生案例分析》的相关规定猎捕隼类动物10只以上属于特别严重情节,应按照《刑法》第1条交通类大学款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且闫某多次实施了猎捕鸟类的行为,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如按照屈学武教授的观点,应对闫某实施的多次猎捕行为按连续犯从重处罚。
所以就本案而言,司法机关已在可裁量的范围内给予了闫某广州大学的刑罚,说明判案法官已经充分考虑了闫某系在校大学生且系初犯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故判处闫某10年半有期徒刑完全正当,也即本案对量刑情节把握准确。
一种观点认为对猎捕、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必须用运用刑罚加以处罚,因为猎捕、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侵害的是生态法益。
此法益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和人类生存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一旦破坏难以修复,且采取其他的处罚方式不足以威慑罪犯。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一些较轻的猎捕、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也用刑罚对其处罚太过严厉,缺乏弹性,有违刑法的谦抑性。
如果可以运用行政处罚等处罚措施对其处罚一方面能实现保护生态法益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更好的实现刑法的功能和目的。
本案中确定闫某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闫某主观方面的认定,二是对于本案犯罪对象的认定。
通过上文对此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得知,在被告闫某的主观方面闫某属“明知”,且存在犯罪故意,在本案的犯罪对象方面被告闫某所猎捕、收购的鸟类确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